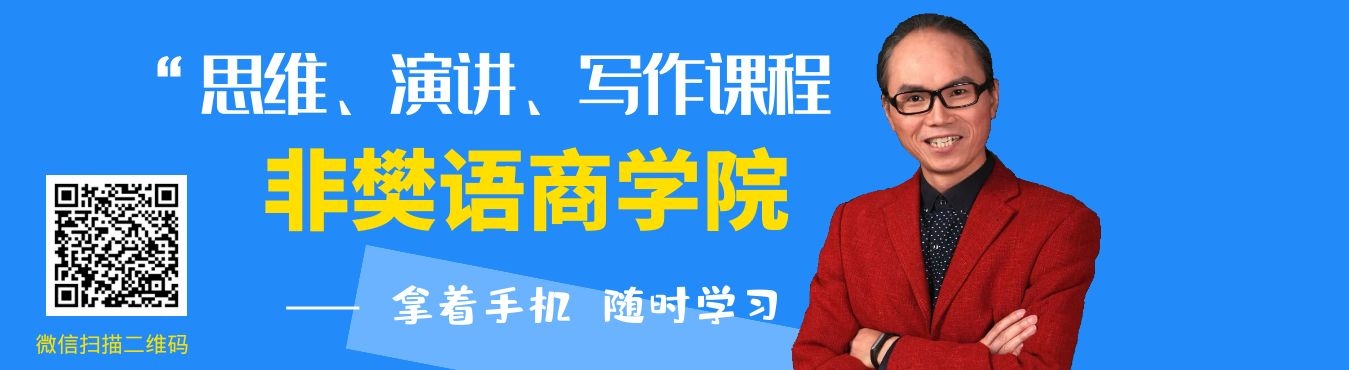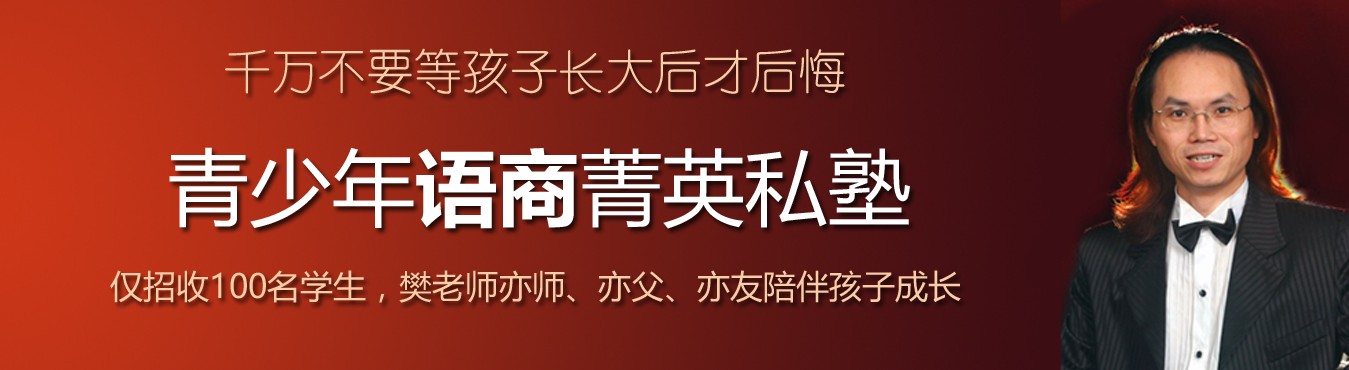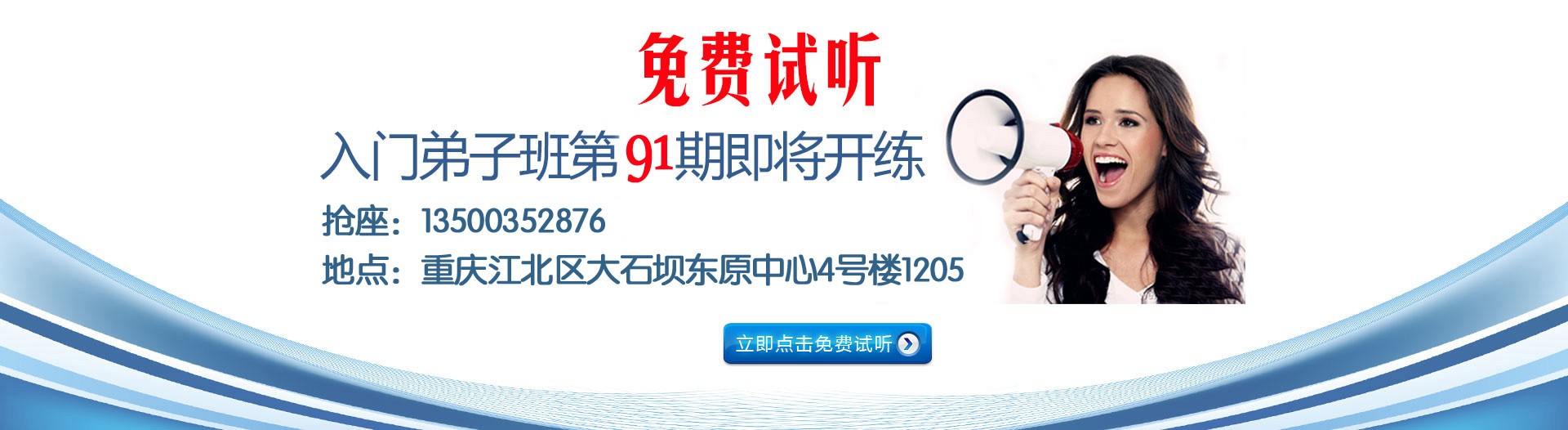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
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,出自《论语·泰伯篇》。根据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断句不同,所得的句意不同。这一争论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句意不同,对孔子的为政思想评价不同。
基本信息
| 中文名 | 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 |
| 拼音 | mín kě shǐ yóu zhī, bǔ kě shǐ zhī zhī |
| 出处 | 论语·泰伯篇 |
| 创作年代 | 春秋时期 |
| 作品体裁 | 语录体 |
| 作者 | 孔子及其弟子 |
| 类型 | 谚语 |
| 属性 | 汉语词语 |
| 释义 | 可以让老百姓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,没必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。 |
原句
出处
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。”——出自《论语·第八章·泰伯篇》“郭店楚墓竹简”(于1993年10月出土)记载版本为:“民可使道之,而不可使智之;民可道也,而不可强也。”
上下文
关于此篇的断句,文学界尚有争论,此处采用一般观点,即用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进行断句。子曰:“泰伯,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让,民无得而称焉。”子曰:“恭而无礼则劳,慎而无礼则葸,勇而无礼则乱,直而无礼则绞。君子笃于亲,则民兴于仁;故旧不遗,则民不偷。”曾子有疾,召门弟子曰:“启予足!启予手!《诗》云:‘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。’而今而后,吾知免夫!小子!”曾子有疾,孟敬子问之。曾子言曰:“鸟之将死,其鸣也哀;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:动容貌,斯远暴慢矣;正颜色,斯近信矣;出辞气,斯远鄙倍矣。笾豆之事,则有司存。”曾子曰:“以能问于不能,以多问于寡;有若无,实若虚,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。”曾子曰:“可以托六尺之孤,可以寄百里之命,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?君子人也!”曾子曰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子曰: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。”子曰: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。”子曰:“好勇疾贫,乱也;人而不仁,疾之已甚,乱也。”子曰: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,使骄且吝,其馀不足观也已。”子曰:“三年学,不至于谷不易得也。”子曰:“笃信好学,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,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。邦有道,贫且贱焉,耻也;邦无道,富且贵焉,耻也。”子曰:“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。”子曰:“师挚之始。《关雎》之乱,洋洋乎盈耳哉!”子曰:“狂而不直,侗而不愿,悾空而不信,吾不知之矣。”子曰:“学如不及,犹恐失之。”子曰:“巍巍乎,舜、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!”子曰:“大哉尧之为君也!巍巍乎!唯天为大,唯尧则之,荡荡乎,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,焕乎其有文章!”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武王曰:“予有乱臣十人。”孔子曰:“才难,不其然乎?唐虞之际,于斯为盛。有妇人焉,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,以服事殷。周之德,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”子曰:“禹,吾无间然矣。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,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,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。禹,吾无间然矣。”
释义
由于古汉语没有断句,所以人们根据现代汉语的习惯,按照不同的断句,对此句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。
释义一
民可使由之;不可使知之。这一句读源远流长,文化大革命用来攻击孔子。如 何晏的《论语集释》、邢昺的《论语疏》、杨伯峻的《论语译注》。古人释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时,一般正面解释。都说,可以 让老百姓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,没必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呢?《论语集释》 只有一句解释“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”,(何晏)《论语疏》解释成“圣人之道深远,人不易知”(邢昺)。路人认为:既然不易知,知起来很 麻烦,所以就不用知了。近代,大都采取批评的态度。范文澜在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中说:“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,可使服从,不可使知之……”孔子政治思想保守。又如 冯友兰在《论孔丘》中说:孔子认为“民”是“下愚的人”,“他们不可使知,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。”孔子鼓吹愚民政策。文革时批判孔子的愚民政策,也大都是引用这两位学者的话。应当说,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句 读成为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没有什么错。但这只是几种可能中的一种。从孔子的一贯主张来看,孔子不赞成愚民政策。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,孔子把一生中的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,孔子有弟子三千,七十二贤人。“自行束脩以上,吾未尝无诲焉”,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,说出这种话的人怎么会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呢?那么古今学者之所以把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句读成为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当代,学者王蔚在《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句意辨析》一文中认为有两个原因。一是没有从整体思想上去把握孔子,这样就有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之感;二是以自己的个人好恶来解释。喜欢者极力为孔子辩解,如何晏与邢昺,不喜欢者则极尽诋毁之能事,如范文澜与冯友兰。好者使其偏,恶者使其冤。路人认为:批林批孔时大批孔子的所谓愚民政策,就是使孔子蒙受了许多不白其冤。还有的人从“民”字上做文章来解释孔子的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。硬说“民”指的是奴隶,既然是奴隶,个人认为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。会说话的工具,当然就不需要“知之”了。持 奴隶观点的 是台湾地区学者。这种解释有两大问题。一、中国古代是不是实行过奴隶制,到当代学术界仍有争论;《孟子》中有关于井田制的记载,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没有实行过奴隶制。二、外国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,中国古代社会是不是这样没有人证明过。至少没有人证明孔子生活的那个时期是如何对待奴隶的。三、即使孔子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奴隶存在,从孔子一贯的主张来看,孔子不大可能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。孔子主张“仁”,仁者爱人。主张爱人的孔子是不会有如此主张的。钱穆先生在 《论语新解》一书中对此的解释也 极有参考价值。原文如下:上章言教化,本章言行政,而大义相通。《孟子》曰: “行之而不着焉,习矣而不察焉,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。”《中庸》曰: “百姓日用而不知。”皆与此章义相发。民性皆善,故可使由。民性不皆明,有智在中人以下者,故有不可使知者。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,必先家喻户晓,日用力于语言文字,以务使之知,不惟无效,抑且离析其耳目,荡惑其心思,而天下从此多故。即论教化,诗与礼乐,仍在使由。由之而不知,自然而深入,终自可知。不由而使知,知终不真,而相率为欺伪。《易传》云: “通其变,使民不倦。神而化之,使民宜之。”亦为民之不可使知,而谋求其可由,乃有此变通神化之用。近人疑《论语》此章谓孔子主愚民便专制,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知之嘅欤!因此钱穆先生的白话译释即是:“先生说:‘ 在上者指导民众,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,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。’”
释义二
断句为:兴于诗,立于理,成于乐。民可,使由之;不可,使知之。孔子的整句话就是说,诗、礼、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,一定要抓好,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,好,让他们自由发挥,如果人民还玩不来这些东东,我们就要去教化他们,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。这种句读最早见于宦懋庸,他在《〈论语〉稽》中解释孔子的这十字名言说:对于民,其可者使其 自由之,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。或曰: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,其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。理解这种方法的 关键是“可”。在这种解释中, “可”是使意动词,认可。与宦懋庸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台湾学者俞志慧。他发表了两篇文章。一是《〈论语·泰伯〉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章心解》(见《孔孟月刊》第三十五卷第五期, 1997年1月号),一是《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章心解补正》。在《心解》一文中,俞志慧通过对《论语》一书中有关“由”、“民”、“使”三字的全部义项和句例的研究,结合儒家仁民爱物、“政者正也”的思想进行分析,认为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句读可点为“民可使,由之;不可使,知之”,指出 其中绝没有什么民愚或者愚民思想,相反,恰恰是儒家德化政治、顺民应天、开启民智思想的体现。应当指出,宦懋庸与俞志慧虽然同意“民可,使由之;不可,使知之。”的句读,但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有所不同。宦懋庸理解的“民可”与“不可”与俞志慧理解的“民可”与“不可”不同。宦懋庸把民分为两类,一类是“其可者”,另一类是“其不可者”。其可者,使其自由之,其不可者也使其知之。其可者与其不可者由舆论判定。而俞志慧对此的看法有所不同。俞把“可”理解成“可以”、“行”,把不可理解成“不可以”,“不行”。即当执政者认为老百姓的道德、行为符合“道”、“礼”的要求时,就随他去,不要管他。如果老百姓的道德、行为不符合“道”“礼”的要求,就要告诉他,引导他。这里,俞志慧强调的“可”与“不可”重点是从是从行为上判断,而不是简单地分类。应当说,俞志慧的解释要比宦懋庸的解释更灵活,更全面一些。应当赞一赞这种句读。因为无论是宦懋庸的解释还是俞志慧的解释,都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与主张。孔子不主张愚民政策这一点是肯定的。因为除了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可以作此解释外,我们从孔子所编的《春秋》,所删定的《诗经》以及《论语》的其他篇章中我们找不到类似的证据。从历史上看,孟子是孔子的忠实信徒,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,主张民贵君轻的人说什么也不会提出愚民主张的。当然,孟子不是孔子,孟子比孔子晚一百多年。如果孔子存在严重的愚民倾向,不会不在孟子的著作里有所体现。
释义三
断句为:民可使,由之;不可使,知之。上面所举的两种句读不同的句子都是讲得通的。但按第一种来解释孔子的话,则与孔子的思想抵牾太甚。第二种虽略近孔子的思想,然此中“可”义模糊,解释者也有不透彻之嫌。其实还有第三种句读方法。即“民可使,由之;不可使,知之。”而第三种句读方法,由于对使的理解不同,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。第一种,把使当作“被支使”、“被使用”“被“驱使”讲,就可以翻译成“老百姓,若可任使,就让他们听命;若不可任使,就让他们明理。”(见 刘LAN英《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别解》一文。)这样才更符合《论语》的语言规律,也更合乎孔子的思想实际。此句读法中,“知”、“由”都作使动词用,“使”字自然属于前面的假设分句,否则便是冠上加冠了!“之”,代词,代“民”。据王力先生的《古代汉语》,“使“在古汉语中有两个基本的意思,一是刚才的“使用”,“支使”,二是“使者”、“出使”。如果作使者讲,那样能讲得通,不过有点笔走偏锋了。学者王蔚在《冤哉,孔子》一文中提出这种观点。原文是这样的:“我们可以把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”句读为“民可使,由之;不可使,知之。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我们可做如下猜想:有一天,国君在向孔子咨询,要派人到国外执行外交任务该怎样做?(我们知道,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,孔子在鲁国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,这种情况是极有可能的。)孔子就告国君,如果有人可以做使者(有出使的条件与能力),就应当授以特权,由他全权处理,不要过多的限制;如果他条件不具备,就应当告诉他,他有哪些方面不足,哪些地方应当改进。把“使”理解成“出使”,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就不是在讨论一般的原则性问题,而是在具体地讨论外交问题。
释义四
断句为:民可使,由之不可;使知之。这种句读是学者王蔚在《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句意辨析》一文中第一个提出。首先,这种句读方法符合古代语法,其二,语意上也讲得通。据此,可这样解释:如果老百姓可以被支使,放任自由是不行的,必须加以引导。孔子一生主张“克己复礼”,孔子一生都在为建立一个礼制社会而努力,孔子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。孔子是主张对老百姓加强领导的。在《论语·为政篇》孔子讲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照此看来,这种解释也能讲得通。只是读起来感觉有些突兀,不大那么顺口。
释义五
断句为:民可使由之?不。可使知之。这种句读也有人提出过,这是最近的事。在2004年8月24日的《语言文字报》上,王昌铭先生撰文提出这种观点。照这种句读,这是孔子在自问自答。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,“孔子说,老百姓可以放任不管吗?不。还是要进行教育。”这种解释不为错。
另解
民“可”,使由之。不可,使知之。人民守法善良的,让他们自主行为不要过多约束。人民愚昧暴戾的,要惩戒教导使其知晓过错。体现儒家博爱、仁德、正义、民主的政治观念。与“苛政猛于虎”相互应证孔子仁慈的内心,与对君子士人的教诲。孔子的言语,多次提及并向往尧舜之治,而尧舜时期天下大同,施行的是挑选禅让制,与现在的民主推选是相同的。孔子多次提及希望生活在尧舜时期,证明其本意非愚民,而是在当时的背景希望君主实现现在的民主。